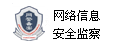最新新闻
热门新闻
特别推荐
渐行渐远的家园
文/邵衡宁
14年了,那两扇铁门一直寂寞地紧闭着,久不开启的大锁早已锈迹斑斑。在冬天晴暖的午后,在村庄如今前所未有的空寂里,我那远在中国苏北平原上的家园,已然成了一只搁浅的舟子。
祖父过世14年了。这座曾经兴旺、热闹近百年的农家四合院,也就空寂了14年。院门深锁,人灭而物毁,时光之手便化草木为尘灰,苍凉荒芜如前朝的废墟:去夏故乡多雨,故居的院墙又倒塌了半边,而半人高的野草,自大门外疯长到四厢房的门坎,微风过处,满院子都是野草欢呼张扬的手臂,成了老鼠、黄鼠狼、蛇和蜘蛛们等小生灵自由出没的天地。
约100年前,这座小院,曾是很热闹的。那时,曾祖父母还正年轻,他们的长子,也就是我的祖父,才刚刚临世。曾祖父母用辛苦攒下的钱,买下了这一亩苇塘,这是全村最低洼的地方,因而便宜。有地就能造房,地势低洼不怕,只要不惜力气,还怕垫不高它吗?
斗转星移,虽然时局动荡,农人的日子难熬,但这苇塘边的家还是一天天兴旺起来了。他们盖起了高大的茅屋12间,每天早晨,宽敞的院子里,曾祖母忙碌地放鸭们、鹅们去苇塘里觅食,在上私塾的祖父的读书声里,二祖父手拿树枝追赶得鸡飞犬跑;而院外,曾祖父正忙着给牲口棚里的牛马喂草拌料。
曾祖父依然每天要从很远的地方推几车土来加高加宽、修补这宅基。这样的“持久战”,一直延续到祖父和二祖父相继成家,苇塘在曾祖父的坚韧里日益被蚕食,那些被垫起的平地上又栽上了些柳树、槐树、杨树、椿树。曾祖父,这家园最初的创业者,就这样日积月累地建设着这片物质基础,使他的两个儿子,能成为村上少有的读书人。
曾祖父母终于离开见证他们一生酸甜苦辣的家园,撒手而去。那时,他们的两个儿子都已成为受乡邻敬重的乡村教师。高大、威严、不苟言笑的祖父,又在他继承的那一半宅基上开始了新一轮的垫宅工程。祖父不只坚持每周日推土垫宅,还每年春上栽树,坚持每月发工资先给孩子们买书。家园在祖父手上依然是12间,只是盖得更宽敞了,成了瓦房。就在这12间瓦房里,祖父将他的孩子们栽培得走出了乡村、去城里工作。
时代的车轮滚动到上世纪80年代末,我们的老宅也更宽更高了——祖父放下的推土车子,又被父亲继承起来,直至我的弟弟们长大成人。父亲一如我的曾祖,一如我的祖父,也重视培养下一代读书,也重视栽树。父亲垫宅已不再为了安居,我们家已安在遥远的外地,他只是为了这是一份祖业、一份承继,或许他是想以此固守一个游子的故乡之根。
上世纪90年代初,家园在父亲的手上又彻底翻盖了一次。6间亮堂堂的大瓦房,坐落在几百棵绿树之中,清晨醒来可听见啁啾的鸟鸣,晚来入梦犹伴着苇塘的蛙鼓,乡邻们都夸老宅院风水好,说难怪这家孙子孙女都有出息!很少有人想到:是整整三代人的坚忍不拔,才垫起这高宅,才托举起儿孙的今日。
但独居于此、故土难移的祖父,那年迈的身影出入在这6间房屋里,就有了些孤寂的意味。笑声和生气只在每年的春节前后,才会弥漫和回荡在这空寂的院子里。那是他在外地读大学、读研究生、当记者、当医生的孙子孙女,又候鸟般地回到了这座家园里。
祖父73岁上终于病倒。自知生命大限已近,他还是花钱请人运了上百车土修补了这祖业宅基。他是希望在他离开了之后,他生前最挂念的儿孙们,还能常回来看看这故乡的根基、这家族的发祥地。
祖父去世后,家园曾经父亲的手翻盖过的,也修缮过的。但无人居住的院落,就像没有灵魂的躯体,毁灭的速度之快令人黯然神伤。
这个岁末,我终于满怀思念千里迢迢地回到了家园,但站在门外,从门缝里看着那些张扬欢呼的过人高的野草,那一种墓地般的破败和荒凉,让我彻底失去了走进去的勇气。
村子里的年轻人和中年人,几乎都涌到城市里务工去了,我只好把钱交给一位年老的邻居,请他代为修缮家园,代为照看。明知道修缮完了,家园还会以让人伤感的速度损毁,但我还是想留下祖上费了很多心血才为我们留下的这份遗产。我总记得祖父的心愿:有这个院子在,你们就总还会想着回到故乡看看;回来了,你们总还有个落脚的地方。
家园常常还会出现在我们的梦里,我们在那里快乐或悲伤。梦之外,家园却渐行渐远。无论我们多么不情愿,都无法阻止它作为一个象征的迅速跌落。
但我没有忘记告诉我的孩子,你的故乡在哪里:那里有一座安静宽大的院子,我的曾祖父母、祖父母,还有我的父母都曾生活在那里,那里是你的根。院落可以被时光锈蚀,而心中的家园,却可以在我们深情讲述中代代相传,依然如新。
载着一个家族向前行驶了近百年的家园,把第四代人渡到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,在最后一个撑船人离开之后,就这样成了一只搁浅的舟子。舟上一切的物品,一切的记忆,都凝固沉没在了过往的岁月里……
【责任编辑:玉倩】
Copyright © 2009平安山东新闻网 版权所有 国家工信部备案:鲁ICP备11014723号-1
E-mail:pasdxw@126.com 本网常年法律顾问:李燕东律师 技术支持:E吧网络
本网站所刊登的平安山东新闻网各种新闻信息和各种专题专栏资料,均为本网版权所有,未经协议授权,禁止下载使用。
电话:0531-82886385 58053779 传真:0531- 58053778 手机:13791124885 QQ:1213285061 通讯员群:
地址:济南市市中区二环南路5861号(山东医专对过) 邮编:250001 公安机关网警备案:37010029002318号
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网络编辑资格培训合格证(2012)第【0285】号
E-mail:pasdxw@126.com 本网常年法律顾问:李燕东律师 技术支持:E吧网络
本网站所刊登的平安山东新闻网各种新闻信息和各种专题专栏资料,均为本网版权所有,未经协议授权,禁止下载使用。
电话:0531-82886385 58053779 传真:0531- 58053778 手机:13791124885 QQ:1213285061 通讯员群:
地址:济南市市中区二环南路5861号(山东医专对过) 邮编:250001 公安机关网警备案:37010029002318号
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网络编辑资格培训合格证(2012)第【0285】号